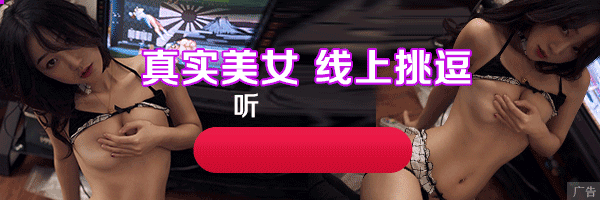你真以为,走个肾就性解放了?

01
中国“性解放”了吗?
这其实是挺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有人曾总结了当今中国社会“性解放”的十八个表现,曰:
男女性道德的规范差距相对缩小;
女性的性主动性、性自觉性和性选择性增强;
性成熟和性行为的年龄大大提前;
惟性主义,即单纯性享乐主义的观念滋长;
性行为的多元形式化,即追求性行为多种多样的浪漫性或刺激性;
各种以性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比从前得以较大的宽容;
以性为对象的各种科学研究得到认可和推广;
在各种媒体上以性为焦点的公开讨论趋于社会大众的认同;
离婚率大幅度提高;
非婚同居率的显着提高;
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
婚外恋的增多;
色/情文学的流传;
卖/淫活动的泛滥;
性/病的重新蔓延;
变相买卖性关系的大量产生;
同性恋的逐渐公开化。
这么丰富多彩的表现,似乎足以证明中国人真的释放了天性、解放了身体。
我就纳闷了,难道中国真的性解放了?
在一个充斥着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时代,在一个“小三”过街人人喊打、“渣男”横行面不改色的时代,我们就这样,“性解放”了?
纳闷之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民国时期的“性博士”张竞生。
02
《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
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
你几岁春情发生?
精几时有?
月经何时来?
你曾嫖妓否?
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
性量大小?
兴趣厚薄?
次数多少?
给我们一个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
如果在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你会不会吓一跳?
这则广告的发布时间,却是1926年。
发这个广告的人,就是张竞生。
张竞生是广东人,是民国第一批留法博士之一,当过革命党人,曾试图营救因刺杀清摄政王入狱的汪精卫。
可见,这位仁兄本来也是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只是去了趟法国之后,就如同吃了春药回来,变成一个立志要在中国“提倡性*自由”的“性博士”。
这个念头,来自于他在法国的风流遭遇。
据他自己的记述,在巴黎,他至少同,西方女人之豪放、之多情、之,让他就像一个忍饥挨饿的穷孩子突然发现了宝藏。来看他的几段如痴如狂的记述:
“在石头崎岖中,在海藻活滑中,我们在颠鸾倒凤时,有时东倾西斜,如小孩们的戏玩于摇床一样的狂欢。海景真是伟大呵!我们两体紧紧抱成一体时也与它同样的伟大。
“有一次,天气骤变雷电闪烁于我们的头上。我们并不示弱,彼此拥抱得更坚固,性欲发泄得与天空的电气一样的交流。我们遍身也是电一样的奔放。可说是:“天光与‘性电’齐飞,‘欲水’和海潮一色。
“你想象我们那时的性/欲真是色胆包天了!当我写至此时,现在尚觉得赫赫然有余威!”
从此,他竟然不再喜欢在房间内做*,而只喜欢野/战了。在挪威的森林,都曾留下他与欧洲妇人酣战的痕迹。
张竞生从此迷乱了,回来后,就满脑子想这也要把中国变成法国。
“在我当时以为这样可以提高男女的情感,得到美满的婚姻。而且我痴心由这样春情奔放,可以生出身体强壮、精神活泼的儿女。
我所希望男女的结合是一种情人制,不是如我国那时的婚姻制。我以为性交能得到自由发展就可帮助情人制的发展;就是把旧时婚姻制打垮了。”
于是,他先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个“爱情定则”:一是爱情是有条件的;二是爱情是可比较的;三是爱情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一言以蔽之:爱情,甚至婚姻,都是可以随意的嘛!
当时的编辑孙伏园趁势就这个话题策划了系列讨论。这场着名的爱情大讨论还吸引了周作人、鲁迅等文化名流参与,论者多持反对态度。
鲁迅倒没有骂他,只是评论说,他的规则 “25世纪或能通行”。
尽管遭到了反对,张竞生还是受到了鼓舞,于是他满怀期待地发了那则征集“性史”的广告。
03
不能不说,当时有些男女,还是比我们想象中要想得开。
不到一个月,张竞生竟然征来了两百多篇稿件,作者有男也有女。他精心挑选了其中的七篇,编辑成册,是为张竞生《性史》第一集,也是唯一的一集。
那七篇文章,无一不是真实记述自己的真实性经历,虽然有些用了化名,但能够公开发表,仍可谓大胆。
其中第一篇《我的性经历》的作者,署名“一舸女士”,不是别人,就是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
她真实地描写了自己童年的性萌动、少年的自*经验和与性体验,甚至比较了第一位和第二位(可能就是张竞生)在身体和性技巧上的区别。
她的描述很细致。细致到什么地步?
细致到了体液。
来看这样一段:
“生产过后,性/欲亢进……故将性机关运动如意,不如先前一味听男子的自动。几度纵送已经排泄了很多的液沫来了,浑身发热,呼吸急促,一阵麻醉,觉得有一股热的液质从子宫口跃出阴*直浇在他的生*器上……这是我可纪念的第一次「出精」!”
张竞生对这篇加了评语,赞不绝口。尤其是对褚问鹃所谓的“液质”,他称作“第三种水”,大赞特赞,大讲特讲,并且后来又专门出了一本书,就叫做《第三种水》。
《性史》第一集一出版,那可真是万人空巷。当时在上海的林语堂曾描写过《性史》发售的盛况:
“出版之初,光华书局两个伙计,专事顾客购买《性史》,收钱、找钱、包书,忙个不停。第一、二日,日销千余本,书局铺面不大,挤满了人,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尤多。巡捕(租界警察)用皮带灌水冲散人群,以维交通。”
后来,张竞生开了个“美的书店”,所售书中多有性学书籍。于是,那里成了流氓阿飞爱去的地方,他们会专挑漂亮的女店员,问她有没有《第三种水》……
就在张竞生出版《性史》6年之前的1920 年,中国最繁华、最洋派的城市——上海的政府还发布公告,说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牢狱之灾。
在这样的一个压抑得变态的社会环境里,张竞生想要推广他在欧洲遇到的那种“可以提高男女情感、得到美满婚姻”的自由性关系,这不是发春梦么?
且不说自古以来东西方在男女关系上的差异,就在当时的中国,三妻四妾仍比比皆是,大街上妓院林立,农村里杀溺女婴,小姑娘上个学校都能成为新闻,女性根本没有地位,更没独立的人格,让她们性解放,是要她们全部都去做妓女么?
像褚问鹃这样的女性,是当时的异类,也是绝少数。
褚出身江南世家,属于五四前后受教育的那拨知识女性,曾在包办婚姻中当过小官僚太太。后来她大胆地出走,只身到山西教书。她在张竞生介绍下,投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与张同居而后结婚。
后来,在大革命中,她进入中共妇女部,成为妇女和左派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也是参与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少数女性之一。后来她进入国民党军中做刊物主编,成为军中第一位女上校。
同属异类的还有下面这两位:
1937年,端木蕻良在武汉遇到东北同乡、作家情侣萧红和萧军。萧军热情邀请他和他们一起住,睡同一张床。随后,萧红开始疏远萧军,最终嫁给了端木。
作家丁玲和胡也频本是公认的一对。有一天,丁玲遇到了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很快爱上了他。纠结中,丁玲提出“不如三人一起生活”,而两位男士竟也答应了。三个人跑到杭州,同居了好一段日子……
这些解放了自己身体的女性,首先解放的是自己的命运。
如果她们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那解放的身体,只能沦为男人的玩物。
04
李银河和王小波
前面说的,都是百年前的陈旧往事。如今怎样呢?
如今,我们也有泼辣大胆的“性博士”,比如李银河。
跟李银河的观点相比,张竞生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且来看银河博士的一些高论:
“一切东西都应该要丰富多彩。如果家庭都只是一夫一妻这个模式,反而显得过于单调。”
“任何人都有和除了配偶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
婚外情是错误的,只是因为它违反了婚姻法。至于一夜*,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对于一夜*的人,我给他们的建议只是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得病。”
“淫*品实际上属于言论范畴的,不是行动。
因为淫秽品,不管是书、录相、杂志,像《花花公子》、《阁楼》,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在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它必须保护这种权利。”
“中国的‘聚众淫乱法’早就应该改了。
我认为,开淫*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
这些论调,高则高矣,然而除了被吃瓜群众做个笑料、被屌丝们当作意淫素材、被卫道士们当作批判的靶子,有谁会真的当真呢?
李银河当然可以去想、可以去说,因为她是社会学家,而她的老公是王小波。
如果她老公不是思想超凡脱俗的作家王小波,而是坊间的普通市民王小三,你让她说说试试。
腿不打断了她的。
可能很多人会说,你瞎讲,现在的中国已经变了。
看起来好像是。就说在男女地位上,很多人都说,现在阴盛阳衰了,不但在家里都是女人说了算,就是在职场,女前辈、女老板、女领导,也是一堆一堆的。
那么事实呢?
在家里,女人也许是可以霸道到让老公跪搓衣板的。可是跪好以后呢?
男人拍拍膝盖走出门去,该约炮还约炮,该撩妹还撩妹。
在职场,很多得志女性的确是风风火火光光鲜鲜,可是光鲜的背后呢?
这两年,拜“汇添富基金”小头目偷情被打、陆家嘴29秒视频、中信证券高管婚外情等等等等事件所赐,大家都知道了金融圈的混乱。
那么,“贵”圈为什么这么乱呢?
有人这样分析:中国主流金融业的高收入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体制红利,很多岗位是溢价岗位。说通俗一点,就是挣的收入大于自己的真实贡献。再说通俗一点,就是很多岗位其实张三妹能干,李四姐也能干。
那么同样作为美女,男上司们为什么把这个岗位给张三妹,而不给李四姐呢?
还不是因为张三妹“懂事”。
很显然,有溢价岗位的绝不止金融行业,有此种混乱的,也绝不止金融圈。
不然,那些贪官们不会各个都顶着“通奸罪”了。
不然,那些教授们也不会总是被喊成“叫兽”了。
不然,那些女演员们也不会总担心(或者盼望?)被“潜规则”了。
这是性解放吗?
不。恰恰相反,这仍是延续千年的性压抑和男权思想遗留下的孽种——
男人说:我有钱,我有权,我就要上你,天经地义。
不给我上?滚。
女人说:你有权,你有钱,我可以让你上,只要你给我足够的好处。
没钱没权还想上我?滚。
如今的中国,仍是男人的天下。不信你可以去留意一下新闻。当中国的政府代表团与西方的政府代表团坐在一起时,你对比一下里头女性的数量。
我数过,许多西方代表团里头女性少的占到三分之一,多的,一半甚至以上。
而中国代表团里的女性,基本上是零,就算有,也是翻译。
男权依然当道,解放从何谈起?
05
究竟什么是性解放?又为什么要性解放?
性解放,是因为有性压抑。
中国人性压抑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从咪蒙体在白领阶层中的大肆流行,从“出轨”、“约炮”的泛滥成灾,还有一直以来以苍老师为杰出代表的岛国女优们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等种种迹象来看,直到如今,性压抑仍是一个常态。
然而性压抑仅仅是性压抑吗?
性压抑的本质,是人性的压抑,是人因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失去了对身体的主宰权。
造成人性压抑的,不是人本身,是整个的社会系统。性压抑是社会的产物,是制度的产物,是道德规范的产物。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它是整个社会系统对个人的一种规训。
社会要你遵守某种规则以维持秩序,哪怕这种规则违背了你的本性。
所以,要解放,解放的也不是身体。相反,身体是性解放的最后一步。
性解放,绝不仅仅是只走肾不走心。那背后,是男权的衰落,是女权的觉醒,是男女走到同一起起跑线之后达成的心灵契约。
性解放有两个前提:
一是女权(女性)的觉醒,二是人格与人际关系的重塑。
女性们要小心,对于你们来说,性解放,绝不仅仅是要从一个“羞涩被动”的女人,变成一个如同男人那样色欲熏心的女人,可以随时找个男人上床,在社交媒体甚至面对面对,讨论男人的丁丁大小。
在曾给美国性解放奠定理论基础的社会学家马尔库塞的理解中,性体验以阳/具为中心,本身就是性压抑的一部分;那除了给男人带来性刺激,什么也改变不了。
女性们要做的,是认识自己,做好自己。
在西方,女权主义由来已久。波伏娃的《第二性》透彻地讲述了女性在面对男性时一直以来的被动地位:“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
她说,“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而得以缓和的方式。”
是社会把女人塑造成了女人,塑造成了被男人掌握、玩弄、胁迫的对象。
她希望女性从此觉醒,做好“女人”。
这本书,让很多女人恍然大悟:原来,女人还可以这样做。所以,它被称为女人的“圣经”。
可直到如今,有几个中国女性读过《第二性》?
如果女人变了,男人也必须要变。
在新的男女关系中,男女之间必须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是简单的财产、权力、工作机会等外在的平等,更应是精神层面的理解和尊重。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性解放可以是一个有用的方式,来促成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的情感重整”,但这有一个前提:私人关系的民主化——包括情侣、朋友、亲子的关系,和塑造它们的人际法则。
在这种“民主化”的私人关系中,一个男子绝不会允许自己以权力去胁迫女性以获取那卑鄙的性欲满足和“征服”快感,也不会为由金钱或职位换取来的女性的投怀送抱而感到快乐;
诚如奥地利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赖希所言:性解放需要人类品性的再造,而不只是多几个“纯洁又放荡”的“新女性”。
也许,我们更应该期待的,是更多“新男性”的诞生。
原文地址:你真以为,走个肾就性解放了?(http://www.99yangshengtang.com/jiankangyangshengtieshi/16762357152273555.shtml)
随机文章
- 失眠怎么办 按这些穴位治疗失眠
- 养胃按什么穴位 按这些穴就对了
- 三阴交穴有什么作用 三阴交的位置
- 晕车按什么穴位 便秘按什么穴位
- 冬季防寒保暖按什么穴位 按这些穴位能保健
- 哪些穴位不能忘 这些穴位能救命
- 按摩穴位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按这里就对了
- 打什么穴位最疼 按摩哪些穴位预防疾病
- 鼻部有哪些穴位需要按摩 按摩这些身体棒
- 头部按摩应该按哪些部位 教你正宗头部按摩
- 女性朋友这些穴位要多揉 教你女性养生穴位
- 长按这些穴位显年轻 教你按不老穴位
- 有哪些穴可以治疗疾病 内关穴的功效
- 按摩穴位有哪些操作方法 按摩穴位技巧
- 承山穴是哪 承山穴可以治什么病
- 为什么我一戴套就变软
-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 男人们常常在性爱中犯的错误
- 老公性冷淡,爱人该怎么办
- 下面的毛毛为啥是卷的?4个阴毛秘密你知道吗
- 每月性生活少于几次才算性冷淡
- 这13种性交痛,42.9%的女性都有过
- 为什么女生性生活到一半总想上厕所
- 古装剧里的那种药,真的存在吗
- 自慰这件事,凭什么女生不行
- 高潮到底有多爽?有姐妹说:大概就是爽哭或者
- 有个需求很强的男友是种怎样的体验
- 无性婚姻到底是种什么体验
- 私处软糖,吃了能让下面变香甜
- 打飞机只用了一分钟的男人是早泄吗
- 别再看A片啦再看你就废啦
- 丁丁不完美照样让你为之疯狂
- 男友丁丁是弯的,怎么回事
- 男人硬度大不如前怎么办
- 如何挑选塑钢门窗
栏目排行
- 20160526我是大医生视频和笔记:李少芬,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炎
- 2018年7月14日播出《书中自有长寿法——经方篇——2》
- 20201202养生堂视频和笔记:王琦,痰,陈皮,橘红,咳痰,流感,化痰
- 《养生一点通》哪种情绪易致病?
- 2016年8月17日播出《健康受损光作祟》,王艳玲
- 20200808健康之路视频和笔记:张雪亮,百合,百合病,百合地黄汤
- 养生堂20181222 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1
- 20220627健康之路视频和笔记:刘健,高血脂,甘油三酯,胆固醇
- 20160314健康之路视频和笔记:陶琳,胃气,胃下垂,气虚,打嗝,呃逆
- 【养生厨房20161027播出】菜名:双耳爆凤翅;
经络穴位大全
中药大全
- 三七
- 当归
- 甘遂
- 木防己
- 八角莲
- 细辛
- 防风
- 白术
- 穿山龙
- 乌药
- 防己
- 川乌头
- 草乌头
- 升麻
- 薤白
- 浙贝母
- 炙甘草
- 山慈菇
- 金荞麦
- 三叶青
- 天南星
- 鲜地黄
- 明党参
- 白附子
- 千年健
- 山柰
- 蚤休
- 拳参
- 胡黄连
- 木香
- 天冬
- 土贝母
- 紫菀
- 白及
- 骨碎补
- 附子
- 续断
- 南沙参
- 牛膝
- 肉苁蓉
- 陈皮
- 黄芪
- 北沙参
- 地榆
- 射干
- 白前
- 贯众
- 天花粉
- 龙胆草
- 金刚藤头
- 毛冬青
- 土牛膝
- 山姜
- 马尿泡
- 知母
- 狼毒
- 锁阳
- 藁本
- 女儿红根
- 延胡索
- 悬钩子
- 酸枣根
- 桑根
- 甘松
- 地骨皮
- 威灵仙
- 光叶海桐根
- 白薇
- 川贝母
- 巴戟天
- 凤尾参
- 三棱
- 曼陀罗根
- 野三七
- 萆薢
- 狗脊
- 百部
- 黄药子
- 甘蔗
- 手参
- 白药子
- 芦根
- 马尾连
- 前胡
- 青木香
- 干姜
- 墓头回
- 虎掌草
- 葱白
- 酸模
- 茜草
- 甘草
- 土白芨
- 姜黄
- 川牛膝
- 黄精
- 高良姜
- 紫草
- 蝎子七
- 小通草
- 广藿香
- 荆芥
- 芫荽
- 白英
- 龙葵
- 半枝莲
- 燕麦
- 紫花地丁
- 瞿麦
- 茵陈
- 肿节风
- 苦地丁
- 八仙草
- 卷柏
- 青蒿
- 牡蒿
- 积雪草
- 大丁草
- 水芹
- 木贼
- 天香炉
- 鹿茸草
- 香薷
- 龙舌草
- 淡竹叶
- 石见穿
- 海金沙草
- 徐长卿
- 伸筋草
- 山椒草
- 水葫芦
- 水飞蓟
- 泽兰
- 老君须
- 迷迭香
- 菥蓂
- 委陵菜
- 大白药
- 地羊鹊
- 野芝麻
- 凉粉草
- 刘寄奴
- 透骨草
- 天泡子
- 绞股蓝
- 问荆
- 苦地胆
- 泽漆
- 辣蓼草
- 寄生黄
- 叶下珠
- 大蓟
- 草苁蓉
- 落地荷花
- 墨旱莲
- 香毛草
- 金盏菊
- 金钱草
- 鹅不食草
- 溪黄草
- 接骨草
- 红景天
- 含羞草
- 虎耳草
- 鼠曲草
- 荔枝草
- 地锦草
- 鸡骨草
- 大金牛草
- 谷精草
- 凤尾草
- 铁苋菜
- 漆姑草
- 蛇莓
- 苦丁
- 老鹳草
- 蜈蚣草
- 蒲公英
- 白花蛇舌草
- 冬凌草
- 翻白草
- 小蓟
- 益母草
- 鱼腥草
- 矮地茶
- 地椒
- 水泽兰
- 佩兰
- 藿香
- 马齿苋
- 仙鹤草
- 矮陀陀
- 半边莲
- 连钱草
- 马鞭草
- 凹头苋
- 车前草
- 小红藤
- 败酱草
- 独脚金
- 王不留行
- 川椒
- 蓖麻子
- 青葙子
- 韭菜子
- 小茴香
- 谷芽
- 苦杏仁
- 水红花子
- 冬瓜子
- 冬瓜皮
- 赤小豆
- 亚麻子
- 菟丝子
- 刺蒺藜
- 蒺藜
- 大腹皮
- 草豆蔻
- 粳米
- 瓜蒌
- 决明子
- 补骨脂
- 火麻仁
- 豇豆
- 橘核
- 无花果
- 香椿子
- 鼠李
- 猕猴桃
- 覆盆子
- 竹叶椒
- 柏子仁
- 吴茱萸
- 紫苏子
- 龙眼核
- 皂荚
- 落花生
- 蛇床子
- 糯米
- 挂金灯
- 辣椒
- 番茄
- 山吴萸果
- 化橘红
- 龙葵子
- 榧子
- 沙苑子
- 车前子
- 使君子
- 刀豆
- 青皮
- 鸦胆子
- 乌梅
- 花椒
- 苦瓜
- 石榴皮
- 马钱子
- 莳萝子
- 白苏子
- 白扁豆
- 山楂核
- 大麦
- 香橼
- 八月札
- 沙棘
- 牵牛子
- 葶苈子
- 油桐子
- 诃子
- 胡椒
- 浮小麦
- 牛耳枫子
- 砂仁
- 木蝴蝶
- 棕榈子
- 白豆蔻
- 麦芽
- 益智仁
- 肉豆蔻
- 肉豆蔻衣
- 望江南子
- 猪牙皂
- 桂花子
- 牛蒡子
- 莱菔子
- 蔓荆子
- 桂丁
- 白果
- 冬瓜
- 金樱子
- 路路通
- 地肤子
- 川楝子
- 罗汉果
- 苍耳子
- 酸枣仁
- 大枣
- 橘红
- 荔枝
- 龙眼肉